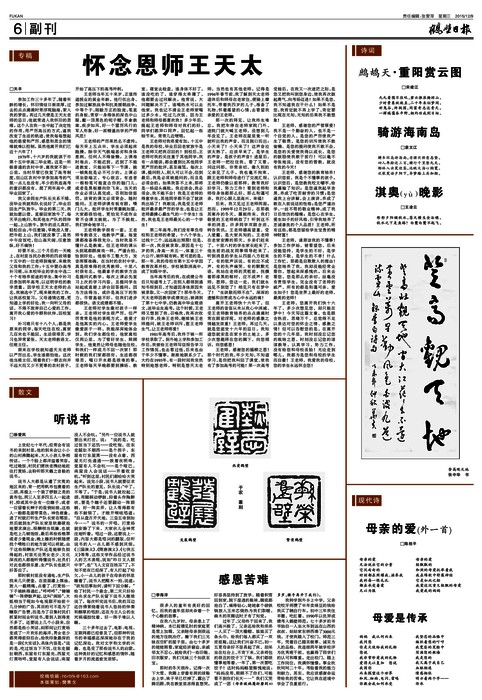听说书
2015-12-08 23:53:20
□徐爱民
上世纪七十年代,经常会有说书的来到村里。他的到来会让小小的山村沸腾起来,大人小孩儿争相传话,一个个脸上都洋溢着笑容。吃过晚饭,村民们便扶老携幼地赶往打麦场,去聆听那天籁之音般的说书。
说书人大都是从遭了灾荒的地区来的,背一把用帆布包裹着的二胡,再提上一个装了锣鼓之类的黄布包,两三人至多四五人一起进村,抑或其中会有一位瞎子,或者一位留着长辫子的俊俏姑娘。这些人一般都是面带菜色,神色疲惫,进了村就打听生产队长家在哪里,然后就到生产队长家里软磨硬泡地要求演出,报酬相当低廉,也就是吃上几顿饱饭,最后再给些粮票或者少量现金,晚上睡的时候随便找个喂牲口的地方就可以将就。由于这些报酬生产队还是能够负担得起的,村里无论男女老少、文化深浅的人都能听得懂说书,社员们对此也都很乐意,生产队长也就只好答应了。
那时候村里没有通电,生产队找来几只便壶,在里面灌上煤油,放入一截棉绳,点着了,打麦场一下子被映得通红。“咚咚咚”、“锵锵锵”一阵锣鼓声起,这叫“闹场”,大抵相当于现如今电视剧开始前十几分钟的广告,其目的可不是为了赚取广告费,而是为了召集村民们抓紧时间去听说书。看到人到得差不多了,还要说上几个小段来,自然都是些小笑话,刹那间让打麦场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,男女老少都笑得前仰后合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段《大实话》,具体内容是:“说的是,吃过饭当下不饥,往东走腿肚朝西,东屋有灯东屋亮,西屋无灯黑咕咚,堂屋有人会说话,南屋没人不会吭。”另外一位说书人就要出来打岔,说:“说的是,吃过饭当下还饥——没吃饱,往东走腿肚不朝西——是个拐子,东屋有灯东屋黑——没有点着,西屋无灯亮通通——放着夜明珠,堂屋有人不会吭——是个哑巴,南屋没人会说话——开着收音机。”听到这里,村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。说完小段,说书人就要征求生产队长的意见,队长说:“中了,不等了。”于是,说书人就拉起二胡,用脚踩动锣鼓,仰着头作陶醉状,要是个瞎子还要翻动一阵眼睛,好一阵卖弄,让人等得都有些不耐烦了,才敞开喉咙唱道:“自从盘古开天地,三皇五帝到如今……”说书的一开唱,打麦场就安静了下来,大家伙儿全神贯注地听着。唱过一段,还要说上一段,内容大都是唱词的翻版,但听说书的人一点儿都不感到厌烦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隋唐演义》、《七侠五义》等等,这些文学作品经过说书人的艺术表现,犹如“昨日文人眼中字”,也“飞入文盲百姓耳”了。不知不觉夜已经深了,有人打起了哈欠,小一点儿的孩子在母亲的怀里睡着了,说书人把醒木一拍,说道:“欲知后事如何,请听下回分解。”给了村民一个悬念,第二天只好纷纷央求生产队长留下说书人继续说了。每次听完说书后,我的耳边还仿佛萦绕着说书人悠扬的伴奏和醇厚的唱腔,还在为主人公的生死祸福担忧着,好一阵子难以入睡。
三十多年过去了,电影、电视、互联网都已经普及了,但那种听说书的幸福感还深深地存在于我的记忆深处。我对文字和文学的兴趣,也是受了那些说书人的启蒙。这种美好的记忆和感恩的情怀,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发浓郁。